都市“騎行族”的生活新主張
如今,在很多城市里,地鐵越修越長、公交越來越多、網約車和出租車也盡在“掌”握,但仍有越來越多的人選擇自行車出行。如今,騎車通勤、騎行周邊游,甚至遠赴新疆、西藏尋找不一樣的自我……騎行儼然成為一種新的生活時尚。

5月15日,一名騎行愛好者在西藏昌都境內的318國道騎行 晉美多吉攝
騎行是一種生活方式
如今,不少人將騎行視為主要的健身方式,只要能騎自行車,就絕不坐汽車。家住上海的周小姐每次出門前都會打開手機地圖查詢路程,只要距離在10公里以內,二話不說就騎車出門。
對于一些資深騎友來說,騎行更是一種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
“像我這么大的北京人都是騎車長大的”,北京市民楊先生告訴記者,“現在騎車對我來說,更像一種生活方式。上下班,以及不算太遠的地方我都會騎車去,舒服、快,不會有堵車時候的糟糕心情。”
“我一直把騎行視作一種生活方式,從小就喜歡在路上一邊騎行一邊思考的感覺,現在上下班來回30多公里,騎車出一身汗,再去沖個澡,絕對精神百倍。”在上海工作的吳心遠說,幾乎是每到一個城市,無論是出差還是旅游,都會先去租一輛單車。
騎行中的詩和遠方
2012年,受一位前輩啟發,吳心遠給一家知名自行車品牌寫了一封郵件,談了很多關于騎行的夢想和熱愛。讓他沒想到的是,一周后,這家公司的相關部門聯系到他,送了他一輛旅行自行車,還送上了一句“祝你完成夢想”。
那一年的畢業旅行,吳心遠一路向南,一個人從天津騎車回到浙江。在長達1900公里的回鄉路上,他見識各種風土人情,“去了很多一輩子再不會去的地方,見了很多一輩子再不會見的人。漫漫長途,經過6個省市,每一米都留下自己的車印和汗水。以至于快到終點時,我根本不想結束。”
當記者聯系安徽小伙楊易時,他正在從廣東騎車前往西藏的路上,剛剛到達一個小城。八千里路云和月,談及為何開始騎行,楊易已經說不太清,他只記得那時創業失敗,極其沮喪。所以,他選擇了騎行,讓自己的身心都能夠放松下來。
如今正在川藏線上奮力騎行的楊易,一路快樂而充實,每天清晨,他只需要知道自己的方向和目標,然后就可以開啟一天的旅行。
吳心遠對此也感同身受,“每一次都有新的騎行體驗。拋下日常的工作,和單車一起被‘丟’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只知道起點和終點,去迎接未知和新奇,那感覺不能更贊。”吳心遠說。
都市治堵新“神器”
除了健身和旅行,自行車也在成為緩解大城市出行難的“新藥方”。
在上海,一種名為“摩拜單車”的共享自行車日漸風靡。與其他的公用自行車不同,“摩拜單車”可以騎到哪兒就停到哪兒。因為自行車上有GPS系統,用戶在手機APP上可以看到離自己最近的可共享單車,然后用APP掃一下車身上的二維碼就可以開鎖。
“摩拜單車”CEO王曉峰告訴記者,現在每天在路上行駛的汽車數以百萬計,但不少車一次出行的車程在5公里以下。“并不是因為大家都喜歡乘車出門,而是因為除了汽車之外,沒有更多的選擇,我們就是要解決這5公里的出行問題。”
顯然,自行車是解決短途出行的不二之選。不過,很多城市對“騎行族”們還不夠“友好”和周到。
周小姐就向記者吐槽,現在上海的自行車道太少太少,一些主要路段根本沒有自行車道。已有的自行車道設計也有問題,不少都是斷頭路,或者自行車道突然變成公交專用道,再過一段路又是自行車道,這既不科學又不安全。此外,自行車道被占用的情況也很普遍,有些道路的自行車道幾乎全都停滿了汽車。
如今,騎行不僅成了一件時尚的事,也因為環保、健康獲得政府的支持和鼓勵,但是,如何讓“騎行族”更自由安全地在城市里騎行,城市管理部門可以做的事情還有很多。(記者 葉健 關桂峰)
城市“蹭網族”:何處安放精神世界
在我們覺得“不可一日無網”的今天,一些流動人群,成為城市里人們并不熟知的“蹭網族”。在大型商場、餐館和一些單位附近經常會出現他們的身影,他們只想蹭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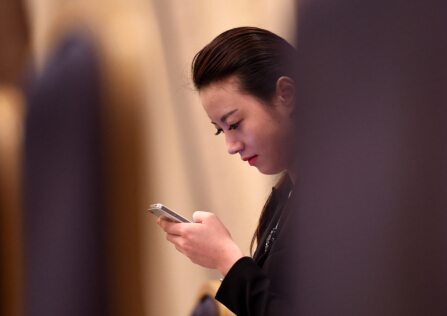
虛擬世界的安慰
手指飛快地在手機上敲打著,不時看著屏幕笑笑,在四川成都市錦江區的一間出租屋里,20歲的李林正躺在床上玩手機。夜幕降臨,這是他每天工作后最快樂的時光。
“工作很累了,回來什么都不想干,就想躺著玩手機。”李林說,睡覺前一般都會打打不需要流量的單機游戲,看視頻、圖片新聞什么的都太費流量。有時他們也會蹭下鄰居的網,但是信號一般不太穩定。
李林家在成都郊區的金堂縣,父母遠在外地打工,家里只剩下爺爺奶奶兩個老人。去年,他開始到城里的餐館打工。“工資不多,但是包吃住,有點零花錢,挺好。”李林說自己很容易滿足。
李林住的這間出租屋位于鬧市的一個老舊小區,是他打工的餐館老板租下來的員工宿舍,十多平方米的房間里,沒有電視,擠了五六張床。屋內燈光昏暗,沒有人抬頭,沒有人說話,屏幕的光亮在黑暗中照亮了每個人的臉龐。
“休息的時候,大家偶爾會一起去網吧打游戲。但是,網吧有點貴,一起去一趟要花幾十到一百多元,我們一個月才掙一千多元,消費不起。”李林說,因為他們都是打短工,也沒人愿意自己掏錢包月包年裝寬帶,關鍵也是為了省錢。
李林說,一個月包月的手機流量太少了。于是,上白班的他和同住的伙伴們經常在收工后去大商場轉悠,“不買東西,就是為了享受免費的WiFi。”他有些不好意思,但隨后又理直氣壯,“商場的WiFi本來就是免費開放的嘛!”
李林說,附近商場、餐館都是他們常去蹭網的地方,有時候會一直待到打烊,回來倒頭就睡。
蹭網的無奈
在廣州一家私企打工的王寧(化名)也是“蹭網族”。不高的工資扣除吃穿住行,所剩無幾。手機費要節省,群租房的網絡帶寬又根本不足以支撐二三十個終端,連接不上網絡是常事。為了能夠暢享網絡生活,王寧有時候下班也會故意拖延,“但也不敢天天都待特別久,怕老板覺得我效率太低,把我給炒了,于是我就經常去商場、飯店蹭網。”王寧說,他特意節衣縮食把家門口不太貴的飯店都吃遍了,就是為了吃飯時方便問到WiFi密碼,“有時實在沒地方上網,又舍不得進去吃飯,就在飯店門口蹭一會兒。”
虛擬世界給李林單調重復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對著手機,就像是找到了另外一個好朋友,在網上可以寫自己的心情,上QQ和陌生人聊天,經常聊到深夜。”李林說,這樣漫無目的、彼此不知身份的聊天讓他感到安全,沒有人知道你每天要洗多少碗,大家說的都是心情,很有共鳴。為了跟陌生的QQ好友多聊會兒天,他幾乎每天都要去附近的商場里蹲著蹭網,“有網有空調,很舒服。”李林說,這就像是他的一個根據地,雖然商場里的人來來往往,但是沒有人注意到他。
蹭網,也有令他苦惱和尷尬的時候。“商場晚上10點關門,冬天更早,時間太短了。”李林說,有時候和網友聊得正火熱,商場打烊了,流量又用完了,不得已下線,第二天下班趕緊奔到商場再上線,對方已經把自己刪了。為了在商場里用起來更有面子,李林還攢錢買了個二手蘋果手機。
在餐館的情況也好不到哪里。“餐館里的服務員都認得我們,見了就給臉色,喊我們快點走。”李林說,這時候,他們就點杯小飲料,一坐就半天,服務員也無可奈何。
對于“蹭網族”來說,蹭網是一件方便又開心的事,但有時會給被蹭網的人帶來一些煩惱。
記者走訪海南省海口市望海國際商場,一些服裝品牌店老板告訴記者,不少“蹭網族”來到店里,看似買東西,試完衣服后便問WiFi密碼多少,然后坐在休息區拿著手機“刷網乘涼”。“我們不好意思催顧客走,店里面積有限,隨著蹭網的人越來越多,就會影響營業,被逼無奈我們只能不斷修改密碼。”
關注流動人群的精神需求
《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5)》顯示,預計2020年我國流動遷移人口將逐步增加到2.91億,年均增加600萬人左右。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發展研究院教授張春河認為,流動人群的蹭網現象反映出當前我國公共網絡供給與需求之間存在脫節,國家還需在硬件設施上盡可能鋪開,加大公共網絡建設投入力度。
方便實惠的同時,“蹭網族”也面臨著一些看不見的安全隱患。
北京中倫(成都)律師事務所律師李心蕙認為,一方面,蹭網很容易造成個人信息泄露,二是如果占用單位WiFi資源,有時候由于手機不小心下載了木馬軟件,在聯網的過程中攻擊并盜取了單位信息,就會比較麻煩。
城市“蹭網族”的背后,是流動人群精神世界無處寄托的困惑。業內專家表示,滿足流動人群的精神文化需求,需要開拓更多的形式和內容,不斷豐富流動人群的業余文化生活。其中,政府購買服務為流動群體提供精神文化服務就是解決之道之一。(記者 董小紅 李金紅)
海外“老漂族”:一切為了孩子
我國已成為留學生輸出大國,隨著在海外工作學習的年輕人逐漸結婚生子,為了照顧兒孫,不少留學生的父母來到異國他鄉,成為海外“老漂族”。不管是短“漂”還是長“漂”,盡管狀況不一,但海外“老漂族”數量的上升趨勢正越來越明顯。

以孫輩需要為第一原則
來自大連的溫之雅與愛人在日本留學工作了10年。今年年初,兒子誕生后,溫之雅的媽媽隨即從大連趕到東京,幫忙照顧外孫。溫媽媽此前很希望女兒女婿能夠回國工作,后來她尊重了孩子們的選擇。
56歲的福建福清人陳國祥沒有想到,自己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是去為外孫女當“保姆”。30年前,陳國祥與許多同齡人一樣,醉心于出國務工。然而由于種種原因,他最終還是沒能拿到日本簽證。
30年后,陳國祥的女婿東京大學博士畢業后,入職東芝公司,女兒則在日本做起了全職太太,專心撫養兩個淘氣的小外孫女。最近,由于大外孫女夜里經常哭鬧,陳國祥決定去日本幫女兒的忙。
“漂”在海外
陳國祥在日本的日子簡單、平靜,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哄外孫女吃飯、睡覺。偶爾跟女兒外出購物,服務員的熱情讓陳國祥有些局促。“試穿鞋子時,服務員跪在旁邊,一邊幫忙系鞋帶,一邊比劃著鞋子各個部位,雖然介紹很詳細,但我聽不懂。”30年前翻爛的日語大辭典,并沒有教會他日語聽力。陳國祥坦言,自己不喜歡外出,因為啥都聽不懂。
每天傍晚,外孫女總會吵著要到馬路對面的小公園里玩。就是這個兩畝大小的社區公園,成了陳國祥在日本少有的與外人接觸的場所。在社區公園里,陳國祥認識了探親期間唯一一位朋友:馬來西亞籍華人老林。老林比陳國祥年長四五歲,原來是做外貿生意的,兒子兒媳在日本工作。這次與老伴一起來照顧生孩子的兒媳。第一次在公園碰見時,老林主動上前打招呼,先是用日語,隨即改口用漢語,這讓陳國祥很親切:總算在日本有一個能夠說話的朋友了。
老林主動介紹了家庭成員、住址后,向陳國祥要了電話,隔幾天就邀請他與老伴、孩子一起吃飯。“日本這邊人生地不熟,我們多認識一下,以后互相好有個照應”,這是老林常說的一句話。回國時,陳國祥說,看著留在日本的女兒一家子,自己腦海中也常常浮現老林這句話。
如今,像老林和老陳這樣被動“漂”在海外的父母慢慢多起來。他們“漂”在海外,負責照料兒孫的生活起居。與年輕人相比,“大叔大媽”們的生活單調、乏味,甚至有些冷清、孤獨。
歸宿還在國內
家住西安的屠女士,今年春節一過就飛到美國洛杉磯給女兒帶孩子,這已經是她第三次往返于國內和洛杉磯了。屠女士的女兒從讀研究生起就生活在美國,畢業后嫁給了當地人,還生了可愛的混血寶寶。
屠女士在美國的生活繁忙而辛苦,從做飯到看孩子,她一個人全包了,為的是不讓上班的女兒女婿操心。即便如此,最初因為育兒理念的差異,屠女士還是和洋女婿產生了嚴重的分歧。洋女婿對岳母用熱水給孩子沖奶粉表示不理解,因為在美國大都用涼水沖奶粉,但屠女士認為這樣會讓孩子吃壞肚子。
時間久了,洋女婿越來越感謝中國岳母所做的一切。屠女士也一直提醒自己,要尊重美國傳統,不干擾女兒女婿的決定,所以家庭關系一直比較和睦。不過,屠女士覺得,雖然在海外生活條件好些,但是對于她這個年紀的人來說,還是有點找不到歸宿的感覺。她表示等外孫大些,自己還是要回國生活。
除了語言不通外,文化習俗、生活習慣等方面的差異讓不少海外“老漂族”比較難以適應。曾在日本工作生活多年的廈門大學日本研究所所長王虹說,準備出國的父母親們最好在出國之前接受一些欲前往國家相關知識的培訓。如長期在外生活,可考慮拜訪當地的華人華僑,向他們討教一些注意事項,學習一些諸如日常起居、出行購物、醫療服務等必要的當地常識,既提高生活品質,也可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記者 劉旸 張曦 陳旺)